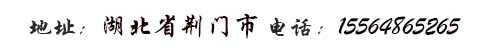名家名作项丽敏野味
|
野味 项丽敏 表姐的观音豆腐 观音豆腐也叫绿豆腐,是夏天才有的野味。 说到野味,总以为是野生动物,比如野鸡野鸭野兔。这样理解也没错,只是狭隘了些。在我看来,只要是野生而又可以食用的滋味,都可归置到野味名下,包括野菜和野果。 观音豆腐就是野菜的一种,但它又不同于通常的野菜,比如荠菜和马兰头,从山里采回家,洗干净炒熟即可食用。观音豆腐在山里是采不到的,采到的只是一种名叫腐婢的小灌木。 观音豆腐就是从这有着清幽香气的小灌木里得来,确切地说,是从小灌木的绿叶里得来,在成为野味之前,还需要一个制作加工的过程。 我也只吃过两三回观音豆腐,是在很久以前,在小时候。 我吃过的观音豆腐是堂姐做的。堂姐是四伯的女儿,比我大八岁,在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丫头时,她已出脱成成熟的少女了,挨近她身边,就能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味道,说不出那味道的来源,只是觉得好闻,像是汗香,又像饱含甜汁的瓜果在盛夏散发的气味。 堂姐读完小学后就不再读书了,家里有两个弟弟,大弟又患有疾病,站着好好的,突然就倒在地上,手脚不停抽搐,嘴角泛着白沫沫。村里人说这病叫羊癫风,胎里带来,没法治。大弟随时会发病,不能出门,还得留个人在家里看护他,在他发病时抱紧他,往他嘴里塞毛巾,用手指掐他人中,不让他昏死过去。 四伯很少落家,长年在外面做事。堂姐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四伯母,身体也不好,病恹恹,干不得重活。这样,家里家外的很多事就落在堂姐头上了。苦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堂姐很小就表现出灵巧能干的特质,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和堂姐同龄的姑娘还在父母跟前撒娇呢,她就当起了家,成了这个家里名副其实的女主人。 堂姐每天要干很多活,砍柴种地洗衣服做饭,没有闲着的时候,即便在夏天的夜晚,别人都坐在院子里,摇着蒲扇乘凉时,她的手仍在忙活,借着月亮的微光,飞针走线地纳着鞋底。 堂姐生来爱笑,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道缝,还喜欢唱黄梅调,边干活边唱。堂姐说唱黄梅调能解乏,干活就不觉得累了。 我家和堂姐家离得近,一天总要往她家跑几趟,吃饭的时候也会端着饭碗跑到她家。在堂姐身边,碗里干巴巴的饭也会变得有滋味一点。观音豆腐就是在堂姐家吃的。堂姐将那绿莹莹又似肉冻般的东西舀到我碗里时,我有点发懵,举着筷子不知如何下口。“吃吧,这是我做的观音豆腐,夏天吃这个好,消暑气。”堂姐眼睛又眯成一道缝,笑道。 我家在夏天也会做一些消暑的食物吃,大多是绿豆汤、藕粉羮,加点白糖,放凉了吃,感觉也不错,但那些都是流质,汤汤水水的,没什么看相。眼前的观音豆腐却是固状的,碧绿通透,厚实中又有颤巍巍的柔软,别说吃,看在眼里就感到不凡。 现在回想观音豆腐,已记不清它的味道了,只记得它出尘脱俗的凉润,还有它毫无杂质的清香——之后许多年,再也没有与这样的清香重逢过。 那不久又吃过两回观音豆腐。有一次是在河边,亲眼看着堂姐制作的。堂姐在河里洗完衣服,一转身,不知从哪里扯了一大把绿叶子,洗干净,放进脸盆,再加一些清水,不停搓揉,直到把叶子揉成细末,把里面的绿汁全揉出来。 脸盆里的液体已变成深碧色,浮着一层白沫儿。堂姐拿出一块干净的纱布,蒙在脸盆边缘,把脸盆里混着叶渣的汁水缓缓倒入洋瓷缸中。这样过滤了两遍,叶渣就全部滤除了。堂姐一手拎着装衣服的篮子,一手端着盛着绿汁的洋瓷缸。我则端着空脸盆,紧跟在堂姐后面。 我迫切地想知道堂姐是怎么把绿汁变成观音豆腐的,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分了一下神——也只是一小会的功夫,就错过了这关键的时刻。就像观看魔术的孩子,眨了一下眼,魔术师手里的丝巾就变成了鸽子。 等我再走到洋瓷缸跟前时,里面的绿汁已经凝固,成冻玉状了。 很多年后,终于知道那使绿汁凝固的东西不过是一把草木灰。将锅灶下现成的草木灰取一小把,入水,过滤,将滤去杂质的草木灰水倒入绿汁,搅拌一会,观音豆腐就做成了。草木灰含碱,有凝固剂的作用。草木灰还可以止血,有次大弟发病,额头磕在桌角上,顷刻淌出了血,堂姐就将草木灰抓一把,抹在他的额头上。 在我小学毕业那年,堂姐嫁了人,嫁得不远,就在邻村。婚后的堂姐依然住在娘家,和丈夫一起照应着家人的生活,直到大弟去世,小弟也学上了手艺,四伯回到家里不再出去,堂姐才离开,住到邻村婆家去了。 差不多过去三十多年了,当我想起堂姐,记忆里仍是她身上好闻的味道,还有她眯缝着眼的笑容,自得其乐的黄梅调,蹲在河边搓揉着腐婢叶子的样子。夏日的阳光照着她长长的脖颈和挂着细汗珠子的脸颊,那么好看,就像照着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春山入盘 皖南山多,野菜也多,多得叫不上名字,不过常吃的也就那么几种,荠菜、马兰头、蕨菜、笋、野水芹、蒿子菜。 荠菜的吃法比较讲究,过年的时候用来包饺子吃,也可凉拌,开水焯一下,切得细细的,撒一些碾碎的花生米,加麻油、盐、姜末,拌匀,即可食之。 凉拌荠菜是一道能上席的菜,适宜用来招待城里的客人,有田野的清气,又入眼,翠生生的,一小盘堆在面前,就是一座春山。 马兰头清炒着吃最好,也可与干丝同炒,菜籽油要多放,我们那里有句顺口溜,“马兰头,炒炒一锅油”,意思是炒马兰头得倒进一锅油。当然,这顺口溜是有些夸张的,表明马兰头很“吃油”,油放得不够,菜就干巴巴,不好看,入口的味道也差了很多。 我家小时候并不常吃马兰头,就是因为它太“吃油”了,我妈平常炒菜只在锅底滴上几滴,有些菜,比如蛋汤,根本就不放油。那时的菜籽油是定量供应,一斤菜籽油得精打细算地吃上几个月。为了吃一顿马兰头,赔上那么多油,是多么不划算的事。 小时候最常吃的野菜是蕨菜和笋,这两种野菜也“吃油”,但它们有一样好处,可以与腊肉同炒,还可晒成干菜,储存在那里。 无论多俭省的人家,腊肉还是有的。家里养的猪,年前杀好,除去过年时吃的,余下的用盐腌上,放在坛子里,压上大石头。过完年后,再把腊肉从坛子里搬出来,挂在屋檐下,吃的时候割一小块。 腊肉里瘦的部分蒸着吃,肥的就用来熬油,炒蕨菜和笋。 腊肉熬出来的油真是香啊,那香是厚实的,富庶的,饱足的,在锅底腾起来,溢满厨房时,倒入切好的蕨菜或笋,滋喇一声,野菜的香跟着腾起来了,和腊肉的香无比亲密地融合,诱得人胃口大开。 挂在屋檐下的腊肉一天天地割着,眼看着就没了,只剩下皮和骨头,这时,就是晒干的蕨菜和笋登场的时候了。吸纳了太阳味道的缘故吧,晒干的蕨菜和笋比新鲜的吃起来更香。 干蕨菜或干笋炖腊肉骨头,算是一道大菜,家里来了客人,或过节的时候才吃得上。当然,那是小时候,现在,只要想吃,随时都可以。但随时都可以吃的时候,又勾不起吃的欲望了。 野水芹的味道最能代表阳春的气息,浓郁的清香,咬在嘴里一股脆生生的韧劲。我妈这几年尤其喜欢野水芹,说野水芹能降血压,每天都提着小篮子出去采,“野水芹现在很难采到啦,田里打除草剂,很多野菜长不起来,不像从前,到处都是。”我妈叹道。 蒿子菜就是鼠曲草,也是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里写的黄花麦果,吃法和文章里写的一样,“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做糕。”我们这里把糕叫做“粿”,蒿子菜做的粿就叫蒿子粿,因为是清明前后才有,也叫清明粿。 清明粿是绿色的,春深时节的绿。吃了清明粿,就是吃下了春天的颜色和味道,眼看着春光渐老,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长在树上的粮食 乌箕子是乌箕树上长出来的坚果。 乌箕树是本地人的叫法,它的学名叫苦槠树,和橡树相似。也有一种说法,说苦槠树和橡树本为一物,南北的差异使它有了不同的名称——在北方,人们叫它橡树,到了南方,它就成了苦槠树。 不管这树的学名究竟叫什么,本地人只叫它乌箕树,爷爷辈的这么叫,父辈的这么叫,孙子辈的也这么叫。话说回来,孙子辈——也就是现在的孩子们,恐怕并不认得这种树了,包括它的果实。现在的孩子难得去野外活动,离自然很远,不像我们那一代,几乎就是野生,把山当做游乐园,与泥巴地里生长的事物打成一片,哪里还有不认识。 在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里,人们与乌箕树的感情是比较亲厚的,对上了年头的老乌箕树更是心存恭敬,扛着长锄走过老乌箕树边,会把锄头从肩上放下来,提在手里,怕不小心撞到了树。忙完活,就摘下草帽,坐在老乌箕树的树荫里,跟树叨咕几句话,叨咕家里最近的愁事、烦心事,也叨咕高兴的事,比如儿媳妇生了娃娃,母鸡又孵了一窝小鸡仔。 村里人家有娶亲的,会去野外砍一根乌箕树枝回来,乌箕树勤于结子,多果实,新房的角落里摆上它,象征着多子多孙。 村里人对乌箕树的感情,说到底还是源于它的果实——乌箕子。乌箕子是长在树上的粮食,不需要耕种就可获得的粮食,如同上天的恩赐,供给村里的人食用,灾荒年月里,还曾救过村里人的命。 乌箕子救命的事是听父亲说的,说他小时候,家里兄弟多,粮食少,总是不够吃,有一年发大水,地里的庄稼淹掉了,到了秋天几乎没有收成,弄得揭不开锅,我奶奶只好上山找吃的。以往的年月里,山上可吃的东西是很多的,尤其乌箕子,到处都是,只要蹲下来就能捡着,捡个把时辰就能把背篓装满,这一年上山却很难见到——不是乌箕树不结果,而是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去山上捡,没几天就捡光了。地上的乌箕子捡光后,就打树上没落下来的,用长竹竿打,打得满地都是折断的树枝。 村头最老的乌箕树也没能逃脱此劫,打得稀里哗啦,一地残骸。奶奶没办法,背着空背篓回了家,家里还存着一些前几天捡的乌箕子,碾成粉,也只够吃三五天,接下来漫长的冬天可怎么过呢? 当奶奶愁得简直想跳河时,却发现,家里的乌箕子没有变少,反倒变多了,甚至还有更珍贵的茅栗——是我大伯弄回来的。奶奶很兴奋,又担心,问他从哪里弄的,可千万不要做丢人现眼的事啊。大伯做了个爬树的动作,说,山上那么多松鼠,掏几个松鼠洞不就有了。 乌箕子的味道其实是有些涩嘴的,若不是遇到荒年,也没人天天吃它,不像松鼠,无论什么年头都以乌箕子为过冬的主粮,大量储存在树洞里。 我小时候,乌箕子就只是饭桌上的副食了,是一道名叫“乌箕豆腐”的家常菜。乌箕豆腐做起来也不算太复杂,把乌箕子晒干,脱壳,磨成水粉,滤渣,沉淀后入锅煮,边煮边搅拌,直到白色淀粉变成褐红的半透明状时出锅,倒入一只洗净的大木盆里,等温度凉下来,凝固成冻状,用刀切成块,加冷水漂着,隔几天换一次水,吃的时候从水里捞一块。 乌箕豆腐在水里多漂几次,苦涩味就没有了,我却不喜欢,乌箕豆腐的好吃,就在那点比较独特的苦涩味上,那是山野的味道,丢掉这味道,它就过于温和,滑溜,和别的淀粉类食物没区别了。 葛根 昨天接一朋友的电话,问我能否买到葛根片,说近来颈椎病犯得厉害。 我说没问题,本地买葛根片容易,街边就有——只知道葛根片有降血压和血脂的功效,却不知这东西对颈椎病也管用。 朋友说葛根片的好处极多,张仲景伤寒论中专治颈椎的方药就叫葛根汤,葛根还可增强记忆,抗衰老。你平时也可泡一些当茶喝,朋友说。 挂上电话,想起书厨里好像就有这东西,我哥放在那里的。去年这个时候他上山挖的葛根,洗净切片晒干,带回乡下给我妈泡水喝,又装了一些在保鲜袋里,留给我。当时我还在北京鲁院学习,腊月回到家,打开书厨,赫然看见一大袋葛根片,塞在书堆中间。 起身去书橱找那袋葛根,翻了个遍,没找到,是叫我给送人了吧?每次收拾房间总要清理出一堆东西,大多是些不吃不用的,放着可惜,还占地方,不如趁没坏时送给用得上的人。 去年腊月看见这包葛根片时还想,我哥也真是,我又没高血压高血脂的,给我这东西干嘛。要是当时就知道葛根片还有治疗颈椎病的功效,就不会觉得我哥多此一举了——我的颈椎也有问题,犯起病来天旋地转的。 我哥喜欢挖葛。也不只是挖葛,所有在山林里钻来钻去的事他都喜欢,拔笋子,打蕨菜,采金银花,采野果……偶尔还会拎回一只野兔。他上班的那个工厂刚好坐落在山中,一到休息时间他就钻到林子里去了,下班回家,摩托车上总带着山货。 我哥带这些东西回家并不讨好,嫂子和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在叫苦,因为要帮着收拾,从四月到五月,差不多每天晚饭后,都得围着一堆小山样的笋子或蕨菜,剥壳,摘拣,洗干净后再过一遍开水,去生。这些山货在山上嫩得很,下了山,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老掉,特别是蕨菜,下山个把钟头就老一大截。有时实在忍不住,对我哥说,明天再不要去弄这些东西了,又吃不掉,还要收拾,真麻烦。我哥不说话,第二天还是拎了满满一袋山货回家,分给左邻右舍。好吧,只要不劳我们去收拾,就随他去吧。 挖葛根是冬天以后的事。立冬以后,家里几乎没断过葛根,切成块状的葛根放在盆子里,吃罢晚饭,我哥用食品袋给装上一些,让我带回自己的住所,当零食吃。 说实话,我从不知道那些葛根挖回来是怎么收拾的,怎么就把那树根一样粗拉拉的东西弄干净,烀熟了,拿起来就可以放到嘴里嚼。我哥从没吩咐我干过这事,这事显然比剥笋子要麻烦得多,指望不上我。只有一次,烀熟的葛根还没有切开,我想,这事不难,我来干吧,就拿了菜刀,切下去——哪里切得动,葛根的淀粉吃住了刀,使上全身的力气,才切进去一点。 葛根挖得多时就拿来洗葛粉,这又是一件麻烦事,好在仍旧跟我没关系,头天晚上,见门口堆着比手臂还长的、沾着新鲜泥土的葛根,第二天下班回家,那些葛根就变成豆浆的糊状,沉淀在一只大水缸里了。 过了几天,葛根粉沉淀好了,滤渣晒干,我哥又用袋子装起一些,让我带走。 葛根片也就是这两三年才晒上的,以前家里没晒过。是大前年吧,偶然听说葛根片泡水喝能降低血压,就跟我哥说了,让他晒一点,我爸我妈血压都高,让他们喝喝,说不定管用。我哥嗯了一声,过几天,一大袋晒得干干的葛根片就在桌上了。 今年家里没晒葛根片,立冬不久,我哥随着厂子整体搬迁到北方去了,也是在山里,只不过那里的山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更没有葛根。 我哥临走前几天还挖了不少葛根,洗了好多葛粉。 我哥走后十天的样子,我下班回家,晚饭后,我嫂指着一个袋子,对我说,那里面是烀熟的葛根,你拿去吃吧。 “葛根,哪里来的?”我问。 “还不是你哥挖的,一直放在杂物间里,也不告诉我,今天整理东西才看见,坏掉了好多。” 我把葛根拿在手上,往自己的住所走去。 天已经很冷了,霜风吹在落尽叶子的树丫上,吹在脸上,有点痛。看着天空的寒月,想着我哥呆在那样一个地方,孤零零的,身边连一棵树都没有,突然就心酸起来。 寒莓茂盛 近来集市上有卖野果的,并不多,遇见了就赶紧走到跟前,怕别人跟我抢似的买下,也不还价,拐枣、羊桃、野柿子、八月炸、九月黄……野果虽其貌不扬,味道却是纯正的,比超市里光鲜的水果更吸引我味蕾。 买它们的另一层原因也是出于怀旧,这些野果对我来说就是童年时光,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看上一眼,哪怕是图片上看见,也觉得亲切,不用吃,妙不可言的滋味就会在记忆里反刍、弥漫,在舌尖漾开。 有些野果集市上是买不到的,比如寒莓,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采寒莓来卖,可能是它太常见了吧,常见的东西容易让人轻慢,觉得不值什么。 寒莓这种野果确实是太寻常了,晚秋初冬时节,只要是走进一条山路,目光随意一撩,就在路边看见它,与金黄的斑茅纠缠在一起,或在落尽叶子的灌木林里四处漫延,如红玛瑙的攒珠串,密集地垂挂着。 寒莓为蔷薇科,悬钩子属,和春天的四月泡、树莓子是近亲,色与味都差不多,只在形状上有些区别:四月泡和树莓子是单生子,独个儿缀在枝间;寒莓则是簇生,聚集成团、成串。摘一串下来,一粒粒地数着吃,吃着吃着,就忘记数了。 寒莓成熟之时是秋色最为华美的时候,每逢此际,就想起普希金的《秋之韵》:忧伤的季节、眼睛的陶醉,我喜欢你道别的美丽——我爱大自然豪华的凋零,森林换上了红色和金色的外衣;林中是风的喧嚣和清新的气息,天空覆盖着波浪般的阴霾,有罕见的阳光、早来的寒冷,还有白发的冬天远处的威胁。 这样的诗句不像是诗人写出来的,更像是上帝的创造,有着自然天成的生命律动。在心里默诵着诗句,沿着水杉和枫香以落叶铺成的小径进入山林,在一只翅膀有些残破、身姿仍旧敏捷的蝴蝶的引领下,忽紧忽慢,越走越深。 阳光如金箔,将蝴蝶的翅膀镀上一层安谧的光,隔一阵子,风便送下几片褐红和金黄的叶子来,叶子以蝴蝶般轻盈的身姿落下时,空中就有梵音升起,树梢上空长久地回旋。 走着,听着,用相机捕捉着,忽然觉得走不动了,像被一个亲熟的友人拦腰扯住,定睛一看,可不是嘛,那扯住自己的正是亲熟的旧友——童年的伙伴——秋阳下分外诱人的寒莓。 和其它悬钩子属的植物一样,寒莓的枝条上是暗藏着刺的,它以刺来保护自己,也以刺和那些经过它的事物打着招呼,若不及时停下,就会被它的刺勾住,亲密又凶狠地咬上一口。 寒莓茂盛之处必有鸟声和流水。寒莓喜阳光,也喜潮湿,而鸟儿们聚集在此则是为了取食,“删繁就简三秋树”,万物收敛的季节,林子里可吃的东西已不多了,而大自然却是恩慈的,在山林的低处,流水的近旁,特意为鸟儿们备下丰足的美味。 直到十二月,大雪落下之前,寒莓都是鸟儿们最好的食物,当然也是我的——当我在山林漫步感到口渴时,就摘下一串,像鸟儿们一样,坦然享受这大自然甜美的赠予。 五味子 图片库里有一张野果的图片,前年初冬拍的。这野果能吃,小时候吃过很多,俗名叫“秤砣”,只是不知道它的学名。昨天偶然就知道了,学名叫“五味子”。 原来五味子就是它啊。 今年春末夏初时,有放蜂人运了蜂箱和帐蓬到这里来,问他怎么这么晚才来,花早开过了呀。放蜂人说,不晚不晚,现在正是五味子开花的时侯,我是来采五味子花蜜的。 放蜂人说这话时,手向身后的山坡指了指。顺着放蜂人的手向山坡看去,满眼青翠,并没有看到花。 放蜂人不是本地人,他怎么就知道这山中有五味子花呢?看来做一个放蜂人也是“术业有专攻”的,除了会养蜂割蜂蜜制花粉,还得在心里存着一卷百花地图册,什么地方有什么植物,什么季节开什么花,都瞒不过他。 对这一带的山野植物,我自以为是比较熟悉的,却怎么想不起五味子花的样子,也难怪,我对这些植物的认识,就像对同一条街上生活多年的邻居的认识,知道他们的容貌、声音,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称谓。 没有同邻居进一步交往的愿望,不知道称谓也没有关系,但对山野的植物,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认识得具体一些,能记住更多的植物名,这样,在山中行走拍摄时,就可以一路叫着它们的名字,那将是多么快乐和自豪的事。 五味子的俗名真是俗——“秤砣”,听起来一点也不象是能吃的东西,毫无美感,不过用在它身上倒是形象,成熟的果子沉甸甸地坠在藤蔓上,可不就象秤砣压在秤杆上嘛,只不过秤砣是黑色,而五味子的果子是红色,生铁在锅炉里烧化了的那种红。 成熟的五味子有香气,并不浓郁,凑近了才能闻到,味道也是淡淡的,山泉水般清冽的甜。 除了甜,五味子没有别的味道了,不像覆盆子,甜中还带着酸。不知道凭什么给它冠以“五味子”这样的学名,“五味子”给人的印象是五味杂陈,如同尘世复杂的生活。也许晒干入药后,它的味道就是另外一种了,与名字相称了。 神农本草经将之五味子列为上品,说它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安神”的功效。我的记忆里并没有人采它制药的印象,只知道它熟透的果子可以吃,味道不错,就算不想吃了,摘几个挂在窗边也很好看。 说起来植物都是可以入药的,以根茎,以果实,以花以叶,对人类身体起着修残补缺的作用。 小时候我也采过草药,在周末或暑假不用上学的日子,跟着大人上山采,采得比较多的是冬青叶、马齿苋、野山楂,还有一种俗名叫“牛奶梦子”的树莓,趁它还是青色的时候摘下,晒干了卖给药店。 有一年暑假,我把卖草药的钱照例交给我妈,我妈没有像以往那样把钱接过去,而是让我自己去买一双凉鞋。 开学了,我穿着新凉鞋去学校,很得意,很有成就感。 要是那时知道“秤砣”也是中草药,且是药中上品,就舍不得吃了,晒干拿到药店,至少能换回一条花裙子。 柿子红了 降霜了,又到了吃柿子的时节。 小时候——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去小伙伴家玩,小伙伴家正在吃柿子,主妇弯着腰,衣袖挽得老高,从盛着草木灰的木桶里往外掏,掏出一只柿子,先捏一下,再放到嘴边吹,把沾着的灰吹干净,递给围在身边的孩子。七八个孩子手里全捧着柿子了,主妇直起腰身,拍拍手说好了好了,到外面吃去,别把汁弄到身上。 孩子们欢呼着跑开,主妇这才看见我,站在一旁眼巴巴地望着她。哎呀,我看看还有没有,主妇说着又把手伸进木桶,掏了好一阵子,又空着手出来。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摘几个。主妇不忍看我眼睛里深深的失望,转身去了后院,很快回来,手里捧着几个柿子。 这是几个又黄又硬的柿子,不像刚才从灰里掏出来的,那么红,一捏就有一个软软的窝。主妇用手帕将柿子包起,让我捧在怀里,说,这柿子还没熟,拿回家让你妈放灰里焐着,焐软就能吃了。 我把柿子捧回家,却不敢交给我妈,我妈早就跟我说过,不准拿人家的东西,不准吃人家的东西。 怎么办?要不,自己找个地方把柿子焐起来吧。 先去厨房里找草木灰,真不巧,锅灶下空空的,草木灰叫我妈给清理了。我着急起来,没有草木灰,这些柿子放哪里焐呢? 后院角落里有堆沙子,堆那里很久了,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没有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蹲在沙堆跟前,挖沙坑,垒沙堡,可以玩出很多花样来,玩很久也不觉得闷。 要不就把柿子埋沙堆里焐着吧? 柿子埋进沙堆后,我很兴奋,又不安,那堆沙在我眼里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它有了光,是“秘密”散发出来的光。 我是个有秘密的孩子了,这秘密让我的小小的心变得敏感起来,有了惦念和盼望。每天趁着大人不在家时,我就把沙堆刨开来,看那些柿子还在不在,用手把柿子轮番捏一遍——捏不动,还是硬得像块石头,就又把柿子埋进沙堆。 过去几天,柿子还是没有软,也没有变红。我有些按捺不住,太想吃这柿子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柿子呢。 又过了两天,我挖开沙堆,拿出柿子,用手捏,觉得变软了一些,可颜色还是黄的,熟了没有呢?——先吃一个试试吧。费力地剥开柿子皮,咬一口,呀,好涩!赶紧往外吐,却怎么也吐不尽,嘴巴厚厚的,满嘴都是细小的颗粒,舌头也变得不听指挥了。 柿子果然还没有熟,估计表皮的那一层软是叫我捏出来的。要焐到什么时候柿子才能变熟呢?我知道熟透了的柿子很甜,“又甜又软,又滑又糯,一吸进嘴里就化掉了”——这是小伙伴告诉我的。 那天下午,我妈把我叫到跟前,拿着一块手帕,问,这是哪里来的? 那是主妇给我包柿子的手帕,柿子埋进沙堆后我就把它丢一边了,忘记送回去。我不敢说慌,低着头,用认错的语气把手帕的来历告诉我妈,把埋柿子的沙堆指给她看。 怪不得整天蹲在这里,真是好吃不要人教啊。我妈装做很生气的样子,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妈把手帕洗干净了,送到主妇家,道了谢,去田里捡来一根芝麻秸,截成牙签大小,沿着柿蒂边插进去,把柿子挨个儿摆在窗台上。可怜那几只柿子已被我捏得满是指印,凹一块,凸一块,委屈地蹲在窗台一小片太阳地里。 真是奇怪,过了一天,窗台上的柿子就变红了,皮也薄了,深吸一口气,能闻着一股清甜的香气。 又过了一天,能透过薄皮看见里面诱人的果肉了。 到第三天,我妈从窗台上拿起柿子,拔掉芝麻秸,揭开蒂盖,顺着蒂盖口把皮剥下一小半,再把柿子放进汤碗里,搁进一只茶匙,递给踮着脚尖、早已止不住口水的我。 项丽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高研班学员。居于皖南太平湖畔,写作散文、诗歌、童话,已出版的作品集有《金色湖滩》、《花森林》、《临湖:太平湖摄手记》、《美好的事物那么寂静》、《器物里的旧光阴》。曾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 让阅读无处不在让悦读丰富人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yuanz.com/wwzzz/2901.html
- 上一篇文章: 桂圆是个宝,可惜很多人不懂怎么吃
- 下一篇文章: 名医厨房安神美味的五味子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