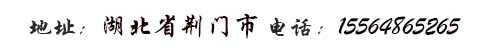楚林散文本草系列
|
点击上方新时代文学研究会免费订阅 楚林(本名周世菊),湖北襄阳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文学院第十二届签约作家。先后在《北方文学》《芳草》《延河》《散文》《饮食参考》《本草生活》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遇见最美的本草——一位临床医生的中药札记》,该书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先后入选第三届全国悦读中医活动“十大中医药好书”,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二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东方卫视《本草中华》栏目为其拍摄专题纪录片。 本草系列散文 ⊙楚林 约定——五味子 五味子成熟得让人嫉妒。秋天去神农架,走到半山腰,遇见五味子。像是谁把一串一串的玛瑙挂在树间,晶莹剔透,光彩夺目。斜斜的阳光下,绿叶纷披,斑驳的光影在为它打造最美的空间。你若看着它,它就会调皮地对你眨着眼睛。但你若忍不住想摘一串,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五味子的藤蔓爬得高兴,想借谁的高枝就借谁的高枝,哪儿会让你够得着。若说秋天的山林是开始走向迟暮的美人,但只要五味子一成熟,那山林的青春就回来啦! 唐代《新修本草》载:“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咸味。”故有五味子之名。这名字有禅意。细品,越品越有味道。古医书称它荎蕏(音chizhu)、玄及、会及,最早列于神农本草经上品中药,具滋补强壮之力,药用价值极高,有强身健体之效。 新鲜的五味子好吃,不仅色相诱人,口感也很美。入口酸、甜,有经霜的清爽和凉意。吃五味子不吐核。吐核的都是外地人,不会吃。核有微微的辛和苦,但核才是精华,越嚼越香。外地人不懂得,一吐核便是五味只吃了三味,差两味。这样的人生便不完美。 山里人最会吃五味子。煮五味子粥自不必说。用自然风干的五味子文火炒至微焦,配绿茶和蜂蜜就是香甜的五味子茶。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冲一杯,酸甜辛苦咸,真的是五味俱全,瞬间就驱除了旅途的风尘与疲惫。如果主人心情好,再奉上漂亮的五味子酒,那你可就是有福的贵客。五味子经清洗、风干、磨碎、炒香、入粮食酒密封,浸足半月,便是美味的五味子酒。泡五味子酒有一个诀窍,就是每天都要抱着瓶子晃一晃。摇晃才能入味。甘酸辛苦咸,晃呀晃,全晃进了醇香的高粱或玉米酒中。高梁或玉米醉了,五味子应该也醉了吧!晕晕乎乎的酒,一天比一天清亮,一天比一天透明,变成了浅浅的宝石红,就好啦!盖子一揭开,满天满地的果香和酒香。这样甜蜜相融,美丽香浓的酒,是爱情,喝一口,能赶走孤单和寂寞,再寡淡的日子也会变得有滋有味。 俗话说五味慰五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五味子虽小五味俱全。中医认为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入肺,咸入肾。猎人一样的五味子,真像你失散多年的亲人,相见恨晚的知己,或者是会偷心的小情人,一不小心就射进了你的五脏六腑,专补你的软肋和泪点。五味子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就像南方人和北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植物也是如此。南五味色鲜红、个头小、果粒小、肉轻薄,偏于敛肺止咳,治风寒咳嗽有奇效。北五味紫黑色、个头大、肉厚、有油性及光泽,最益补心肾,治虚损劳伤最妙。南方人常说南五味好,北方人则说北五味好。其实都是好药,有一句诗说,南五味,北五味,南北五味慰五脏。解的就是这个纷争。 晋代葛洪《抱朴子》曾载:“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淮南公羡门子服之十六年,面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葛洪笔下的五味子真像是一个美丽的神话。其实,我也常常觉得五味子是不真实的。它像雨后的彩虹,是天空最美的梦。譬如,古书上说五味子治“黄昏嗽。”“黄昏嗽”是指人在近黄昏时咳嗽加重。元代名医朱丹溪《丹溪心法》:黄昏嗽者,是火气浮于肺,不宜用凉药,宜五味子、五倍子敛而降之。这哪里像是在治病,应该是在赴一场黄昏的约会。收敛,肃降,静心。关于健康与生命的某个密码,在貌似一杯佳茗的袅袅清香中被慢慢破译。还有,药王孙思邈说:五月常服五味子以补五脏气。遇夏月季夏之间,困乏无力,无气以动,与黄芪、人参、麦门冬,少加黄檗煎汤服,使人精神顿加,两足筋力涌出。这当是孙思邈和五味子定下的五月之约吧! 我和五味子也有着不期然的交集。那是高考的前几天,最爱临时抱佛脚的我秉烛夜读,却不小心贪睡,烛光点燃蚊帐引发宿舍火灾。不仅自己蚊帐、棉被烧坏还把上铺和临铺的床上用品也烧得一塌糊涂。父亲黑着脸,瞪着眼睛要揍我。母亲边哭边叹息。床单、被罩、棉被、蚊帐、衣物等,折算成人民币要赔给同学几百元,相当于家里大半年的收入。大人心里难受,我也吓蒙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开始流泪、失眠。一上床便烙煎饼。料事如神的母亲,神一般的在高考前一天送来一瓶糖浆。紫红色,稠稠的,酸酸甜甜。问母亲是什么?母亲说,是五味子糖浆,安神,补脑,考个好学校,什么损失都补回来了。 人生的五味瓶第一次被我打翻,却又被神奇的五味子糖浆一一拾掇起来。禅师一样的五味子,早已修行得深谙人生百味了吧! 星云大师说人生有五味——童年的时候是美味、青年的时候是甘味、中年的时候是苦味、老年的时候是涩味、修行的时候是禅味。一定是修行不够,现在的我依然会失眠。感情上的烦恼,工作上的不顺,人到中年的恐慌,思念至亲的心痛,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琴棋书画诗酒花的磕磕碰碰……这一切都会让我失眠。无奈的我只好一直延续着和五味子的约会,抑或,它终是我不能舍弃的约定。在许多清风习习月光如水的夜晚,我们素颜以对赤诚相见。我相信,我们一定彻夜长谈过。因为在无数个清晨醒来的时候,我的眼角总是会有一滴泪珠。晶莹、透明、清凉。滑入嘴角,涩涩的,有甘、酸、辛、苦、咸的味道一波一波的涌来。 剪——剪春罗 新春时节,书画家林大学老师赠送一幅字:谁把风刀剪薄罗,极知造化著功多。飘零易逐春光老,公子樽前奈若何。整幅字清新空灵,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这首古诗是宋·翁广元的《剪春罗》,起句便问是谁用风刀剪成薄罗般的花朵,原来都是大自然的极致神功。美丽的花朵让诗人触景生情,想到春光易去,花自飘零,遂劝青年人要珍惜大好时光,不可只知杯前饮酒作乐。林老师说,冬日午后偶遇此诗,提笔即一气呵成,因见诗名为一味中药《剪春罗》,故送之。心细如此,让人感动。 剪春罗,这名字真是起得极美,典雅,生动。可动可静,看着就是一幅春光烂漫的画儿。当然,剪春罗花儿,也是担得起这个名字的。如大多数的石竹科花儿,单层、简洁、大红色,小而艳丽。由春至夏,花开不绝。花圃之上疏林之下,远看繁花似锦,一朵挨一朵,一模一样的笑脸,轻浅温静,甜美可爱,分不出谁是谁。近看,那些薄罗般的花瓣,如少女额前的齐刘海,全都对镜细细地修剪过,每一朵有着每一朵的微妙与精致。 剪春罗。剪出了一朵又一朵美丽的青春时光。最绝的就是这个“剪”字。“剪”当是属于女子的。每一个女子的化妆盒或针线包里都会藏着一把剪。我也是。小学的时候,就偷偷地从母亲的箱底里摸出了一匹布,五光十色的粉红色绸缎被面。关起房门,想给自己裁一条及脚踝的长裙。手握剪刀,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窗外有小鸟的脆鸣、初春的阳光,还有一缕一缕的春风拂过。内心是紧张的,拿一条旧裙比了又比,终于下定决心,闭上眼,带着悲壮的表情,一剪刀下去。一条在那个时代珍贵无比的被面就这样被我毁掉。一顿暴打,却没有丝毫悔意。当然,也剪过刘海儿,第一次给自己剪刘海儿,斜睨着镜子,左手扯紧青丝,右手握紧剪刀,透着丑小鸭将要变成白天鹅般的希望,一剪、又一剪,颤颤抖抖地剪完。左手一松,再照镜子,没有漂亮,反而更丑,哭了起来。短了,剪得太短,白白的额头都露了出来,难看极了,却无法补救。奶奶过来了,说,傻丫头,比着长,穿着短,下剪前,要留几分。 第一次,谁会知道要留几分呢? 奶奶当然知道,她把黑发都剪成了白发。她针线篓里的剪刀又大、又长,特别重,我拿起来都费劲,她却得心应手,娴熟自如。奶奶拿着剪刀,手指细而瘦,如秋后忍冬的藤,边比划边说,好日子是剪出来的。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衣服鞋帽,春夏秋冬,都是奶奶一剪一剪,一针一线连接而成。奶奶还有一个绝活,就是剪窗花。新婚的人家请她去剪双囍、鱼儿扑莲、麒麟送子和鸳鸯戏水;大寿的人家请她去剪大大的福字、剪寿桃、剪富贵牡丹和如意灵芝;新年的时候更热闹,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民间故事都跳进了奶奶的窗花,再跳到家家户户的窗棂上,跳进一个个欢欢喜喜的心坎里。 因为一把剪,奶奶被村人敬重。在农村有句俗话:“找媳妇,要巧的。不问长多好,先看手儿巧。”舅爷的第一次婚姻磕磕绊绊,一遇到槛儿,就会来找奶奶,吃花生米、喝闷酒。奶奶边纳鞋底边慢悠悠地说:“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是一剪子,长痛不如短痛。棉花要摸丫,桃树要剪枝。电影好看,那都是剪出来的。”放下酒杯,舅爷终于在一个春天的午后痛下决心,剪。 以前看古装戏,深闺内的女子在遭遇强盗或强行施暴的小人时,都会突然从袖内或是枕下抽出一把小小的剪刀,目光凛凛,寒光闪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把剪刀,无意中就成全了一个女子的尊严和清白。所以,柔弱的女子都要有一把剪,放在最不为人知的角落。平日里,轻衫裁夏葛,薄袂剪春罗。关键时就是兵器,是可以一招封喉的玉剑。 在妇产科实习时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次是在产房里,第一次操剪为婴儿剪脐带。婴儿粉嫩粉嫩的,鲜红色的脐带,可清晰的看到小血管正在跳动。紧张地握住剪刀,恍惚听见自己的心比小血管跳得还要快。扎紧脐带,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剪,“咯嚓”一声,断了。婴儿“哇”地大哭起来,我吓得手一松,剪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以为是自己剪疼了他,惊恐万分。带我的老主任说,不要怕,婴儿哭是开始呼吸,哭了才好呢!还有一次是在病房里,一位患有晚期子宫癌的老太太,慈眉善目地拉着我的手说:“丫头,你和我说说,我到底还能活多久呢?”看着老太太恳切的眼睛,我不敢隐瞒,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可能就三个月吧。”谁知老太太一听,就扑倒在床嚎啕大哭。明白自己说错了话,我吓得转身就跑,逃出病房。到了办公室,我也哭起来。老主任弄清原委,语重心长地说:“下次可要记着,和有些患者说话时要留几分。” 留几分。这不就是小时候奶奶常说的下剪时要留几分吗。该剪的要剪,该留的要留。所有的事情原来都是这一个理。裁衣、画画、写字、做文、行事、为人等莫不如此。 谁给剪春罗起的这个美名呢,该不会就是李时珍吧?《本草纲目》里对剪春罗的药用叙述最为简洁——气味:甘,寒,无毒;主治:火带疮绕腰生者,采花或叶捣烂,蜜调涂之。 火带疮就是带状疱疹,又称作“蛇丹、蜘蛛疮”。发作时一群密集的小水泡如腰带,或缠腰或缠胁或绕颈,灼热疼痛,异常难受。乃热毒入侵,肝经郁火而致。一朵一朵美丽的剪春罗似乎就是专为这群恶毒的小水泡而生。寒凉如春风,一剪一剪,剪破这些毒疱疹五彩的梦想。 人生恰如剪春罗。不要太多,专注一件事,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即可。如我那用剪出神入化的奶奶;如我一直敬爱的“送子观音”老主任;如多年来专攻书画,精益求精的林大学老师…… 相见欢——吴茱萸 儿时嘴馋贪吃,闹过不少笑话。有年夏天,村里来了一个小伙子卖冰棍。大人不在家,我自作主张拿了五个空酒瓶外加两个鸡蛋换回十块冰棍。十块冰棍啊,太解馋了,一会儿工夫就全进了我的小肚子。到了晚上,肚子里的冰棍开始发威。头痛、恶心、呕吐、吃什么吐什么。到了第二天就更严重啦,又吐又泻,缩成一团,上气不接下气。母亲慌了,让在外做工的父亲快点回来。父亲一看就说,没事儿,这是掉进吴茱萸汤症里了。母亲开始麻利地煎药,一把吴萸、二把红枣、三块生姜、四条党参。父亲说,本来要用人参的,可惜没有,只好用党参代替。 药汤放至温热,受够折磨的我听话地双手抱起药碗喝进一大口。谁知刚入喉“哗”的一声又吐了出来。太难喝啦!苦、辛、辣、臭,说不清是什么怪味。这味道喝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喝。母亲自然不依,捏起鼻子,强硬地给灌了进去。药一进去,没多久就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醒后方知,又捡回一条小命。 吴茱萸于我并不陌生,俗称臭辣子树。在我们村子西的水井旁就有一株,很粗,一个人勉强能抱住。树不高,树叶皱巴巴的,三月树梢开紫红色细花,入秋变成小红果,一族一族,像举在空中的小火把,很好看,但走近后有辛辣刺鼻的气味。树叶、碎花、小果常常会被风吹进井水中,打水时要捞半天,很讨厌。问大人为什么不把这污染水的树砍掉,大人们却说我们傻,不懂事。据说很多年前村里流行瘟疫,后经高人指点才在井边种上此树。叶落井中,可辟鬼魅,除瘟疫。 九月九日这一天,吴茱萸树下最热闹。采茱萸。长竹竿绑着弯镰刀,老人和小孩居多。一族一族的茱萸果子都被勾了下来,鲜红鲜红的,很诱人。一家分一大堆,可惜不能吃。有老人把茱萸枝也掐几枝,插在头上,一路摇摆不停,看着非常有趣。“避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采回来的茱萸被缝进小布包是谓香囊,妇女儿童人人发一个戴在胳膊上。没用完的茱萸阴干,随用随取。村里有小孩受风肚子痛,用茱萸粉调黄酒贴肚脐。还有用茱萸粉调醋贴脚心,治流鼻血、扁桃体发炎、口腔溃疡的,是谓引火归源。我见父亲用得最多的是做“吴茱萸膏”。先把风干的茱萸捣碎,压成粉末。再把凡士林加热,变成滚烫的液状后,倒入茱萸粉使劲搅拌。搅匀放冷后就是“吴茱萸膏”。治湿疹、溃烂、流水的皮肤病都非常好,治“香港脚”也很有效。 九月九日采茱萸。最早见于南朝梁人吴均所作志怪小说《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据说点拨桓景渡过此劫的费长房学过医,能辨众药。 关于吴茱萸为什么姓吴,也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春秋战国时代,吴茱萸原生长在吴国,称为吴萸。有一年,吴国将吴萸作为贡品进献给楚国,楚王见了大为不悦,不听吴臣解释,将其赶了出去。幸亏楚国有位精通医道的朱大夫追去留下了吴萸,并种在自家的院子里。一日,楚王受寒而旧病复发,胃疼难忍,诸药无效。此时,朱大夫将吴萸煎汤治好了楚王的病。当楚王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前往吴国道歉,并号召楚国广为种植吴萸。为了感谢吴国,楚王把吴萸更名为吴茱萸。 虽然被吴茱萸救过一次,可我对吴茱萸还是不待见,因为它的怪味儿。学医后,临床上常常遇到掉进“吴茱萸汤”症候群的病人:男人喝啤酒引起胃痛或疝气发作,女孩子受凉痛经,中年女性月子里受风头痛……让我惊讶的是,吴茱萸汤的效果特别好。无论是阳明寒呕、厥阴头痛、少阴吐利都作用神速,屡用屡效。只要是体内虚寒,不论哪条经络,它的辛、苦、热、辣都能迅速窜达。这些神奇的疗效对一个医者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自此,我开始对吴茱萸刮目相看。现代人体内虚寒的病人特别多。雪糕、冰淇淋、饮料、啤酒、空调、低腰裤、超短裙等等都是它的帮凶。特别是对于原本就属阴性体质的女性来说,温暖的吴茱萸简直就是不可缺少的“妇女之宝”。 离家在外工作日久,竟和大诗人王维一样,患了思乡病。“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古人常于重阳之日,登高畅游,携茱萸女,插茱萸枝,佩茱萸囊,喝茱萸酒,吟茱萸诗,极尽欢娱之乐。故在重阳之日会特别思乡。再看古人之诗,茫茫的乡愁里竟似带有茱萸之温之暖。不知家乡水井旁的茱萸树是否还安在?“他时头似雪,还对插茱萸。”若是九月九日能再去采茱萸,也要“醉把茱萸子细看”,还要掐一枝插在头上才好。 看记者采访著名的乡愁诗人余光中,年近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活力四射、幽默辛辣。他说:“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真是掷地有声。因生于九月九日,有人庆幸他生在这样一个“有诗有酒的日子”,他却说:“在我的艺术想象之中,我生于那一天,那天登高好像是一种壮举,其实是避难,和书中记载的那个桓景一样。而我小时候又碰上了中日战争,因此我把它们联想在一起,我的生日根本就是一场延长的逃难而已。中国人又把自己的生日称作母难日,所以我把自己想象成‘茱萸’的孩子。”“茱萸的孩子”,好生动好贴切。看到此,想自己从小喝着茱萸叶泡过的井水长大,又受过茱萸的救命之恩,何尝不是“茱萸的孩子”呢! 前几日,又近重阳节。朋友邀去登山,美其名曰“闲听竹叶曲,浅酌茱萸杯。”没想到,在山顶,朋友真的带去了酒,一瓶红红的茱萸酒。入口依然是辛、辣、刺鼻,可咽下之后,却犹如一股暖流注入脾胃,半晌之后还有芬芳的醇香在齿间萦绕,绵绵不绝。一杯未完,已经醉了。在它乡,和茱萸以这样的方式肝胆相见,是安慰,也是幸福。相见欢。 END阅读推荐 爷爷最后的日子 静谧的海参崴 荆山草木(六) 忧伤的六月 女猎手(五十五) 沧浪悠悠小三峡 中韩两襄阳缘何“地同名、民同俗” 天子湖夕照 开标志车的壮汉 茅山绷鼓,绵延不息韵悠悠 跪下 乡村晨鸣 清风 夫妻四季歌 清明抒怀 我的石头村 覃裁缝和谭裁缝 ●关于我们 《新时代文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eizia.com/wwzyc/6228.html
- 上一篇文章: 6月6日,苗木求购
- 下一篇文章: 99失眠者有救了休学少年亲历就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