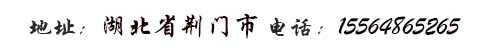兰仓小说五味子子规声声
|
子规声声 由北京西站发往天水的列车奔驰了整整一夜,车窗帘缝隙里开始透进些淡淡的曙光,坐在第八节硬座箱里的肖旺来低头看看怀里迷睡中的女儿姣姣,泛着青晕的眼窝里潸然落下几滴泪。旺来怎么也不会想到,命运对他竟是如此不公,媳妇没有了音信,唯一的女儿又患上了肺结核,要不是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活在世上,他早不想活人了。 心力交瘁的旺来揉了揉干涩发胀的眼睛,看见女儿姣姣的眼角粘着一点眼屎,便用右手小指轻轻的去抠,姣姣起着干痂的嘴角抽动了一下,旺来赶紧从座医院里那位姓康的护士长送的娃哈哈饮料,小心翼翼喂给姣姣,姣姣嘴角抿了抿,喉咙深处幽幽的飘出一声呼唤,妈妈!旺来只觉得心里一阵绞痛,尽管咬紧了牙关,但泪水还是汹涌了下来。 旺来的媳妇翠花是肖家湾最漂亮的女人,那眉那眼那身段属于只要是男人见了就会想入非非的那种女人,从部队复员后当上村民兵连长的建生曾在私下里炫耀说,翠花是天生的尤物。那是年的腊月,在时任村支部书记的父亲操持下,肖家用两千元的彩礼给十九岁的旺来娶来了邻村柳林寨和旺来一起念过初中的女子柳翠花。新婚之夜,等一帮闹完洞房的伙伴嬉笑着走后,旺来被母亲又掐又拧地推上了铺着羊毛毡的新炕。分别放在箱盖上和窗台上的两盏用红墨水瓶做成的长命灯飘忽着橘黄的光焰,屋子里弥漫着迷幻般的色彩。坐在炕旮旯阴影里的翠花羞云满面的斜睨一眼手足无措的旺来,“嗤!”,唇缝里飘出一声浅浅的笑。旺来歪头瞄了一眼翠花,正碰上翠花那火辣辣的目光,慌得忙又垂下了头。时间在一分一秒消逝,翠花见旺来一动不动地靠窗坐着,把脸转向一边羞答答地说不早了,睡吧。旺来垂着头似答似问地说,咋睡。看你咋睡,我先睡了。翠花斜剜一眼旺来,扯过一床红缎被蒙头顾自睡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乡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旺来听说是宽银幕彩色武打片《少林寺》,等不及全家人吃完晚饭,夹着个小板凳去了绷着银幕的村口打麦场里。旺来看完电影回来,一进院门见自己住的西厢房里亮着灯光,屋子里有说话声,等他推开半掩着的屋门,看见从部队复员回来不久的建生坐在炕上抽着纸烟,翠花脸上红红的,眼睛里蒙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波彩,旺来突然发现翠花很迷人。建生一见旺来,从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恒大牌香烟递向旺来,说是专门给旺来留的一包好烟,今晚抽空送来,不巧旺来去看电影了,让他等了大半夜。旺来和建生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谝了一阵,建生瞄一眼翠花,说你俩睡吧,我闲了再来,嘴里哼着“日落西山红霞飞……”出门走了。建生一走,翠花摆好她和旺来的枕头,边脱衣服边柔柔地说,睡吧。旺来脱掉母亲做的对襟棉袄,穿着贴身汗衫小心翼翼地睡在了翠花身边,翠花身上一股让人心醉的气息撩得旺来浑身一阵阵发酥。旺来正在烦躁难耐之际,翠花突然翻转身,脸对着旺来说,穿着衣服睡觉你不难受吗?脱光了睡才舒服哩。口里说着,柔嫩的手臂向旺来的脖颈伸来,旺来只觉得一股热血“轰”一下直冲头顶,一头钻进了翠花怀里。打那晚起,旺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建生也成了旺来家的常客,几乎晚晚过来串门,风雨无阻。渐渐地旺来和建生成了不分你我的好朋友。旺来父亲因为是村支部书记,经常要接待乡上来的干部,有时还要陪着乡上下来的干部到分布在几个沟的村民小组检查工作,很少顾上家里的农活,勤快的建生就常过来帮旺来干些给牲畜铡草掏猪圈的活,特别是一到种麦碾场掰苞米等农忙时节,建生总是不请自到,丢下自家责任田的活来帮旺来,耕地撒麦种的吃力活抢着干,旺来心里感激之余常有一种过意不去的感觉。旺来父母亲私下里常念叨,建生这孩子灵动勤快。 翻年春上的一天下午,旺来、翠花和建生从地里种苞米回来,从乡政府开会回来正在上厅房里煨罐罐茶喝的旺来父亲把建生叫进了屋里,对建生说,民兵连长的位子一直空着,建生当过兵,又是正儿八经的初中毕业生,经支委会研究,准备让他来担这副担子。建生一听,感激涕零的连着叫了几声老爸,忙从自己衣兜里摸出一根纸烟递向旺来父亲,我听老爸的(这里的人有个称谓习惯,把和自己父母同辈的男人通称为爸,女人则通称为阿姨,有特定亲属关系的称谓除外)。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人们从架在旺来家门口大榆树上的喇叭里听到了关于肖家湾党支部村委会任命肖建生为村民兵连长的通告。建生从此成了肖连长,来旺来家的次数也更频繁了,给旺来家干起活来也更加卖力了。 转眼到了年正月,旺来父亲已于几年前作古,女儿姣姣已上小学四年级了。一天,翠花对旺来说,建生媳妇彩梅过两天要去北京,她想约我一起去,活计有她联系。旺来一想这确实是一条挣钱门路,这几年村子里好多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北京当保姆去了,一个比一个挣的钱多,建生媳妇彩梅当了两三年保姆就盖起了小洋楼。翠花刚到北京时,几乎一天给旺来一个电话,说她想旺来想孩子,有时晚上想的睡不着觉。旺来强忍着内心那份思念的煎熬,安慰翠花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惦记他和孩子,慢慢就习惯了。以后的日子里,翠花的电话果然渐渐少了,有时十天半月来一个电话。腊月的一天,旺来接到翠花一个电话,说她给家里寄来了五千元钱,她今年不回家过年了,主家要她陪着到俄罗斯去谈一笔生意,让旺来不要胡想,人家的女人孩子都去。还说以后她可能不方便给家里打电话了,家里也不要轻易打她的手机,人家是有名的大老板,电话太频繁人家不高兴。旺来一听翠花不回家过年,心里虽然有点不悦,但翠花那软软的、犹犹豫豫的声音又惹得他的心软了,忙安慰翠花,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只要你在外面混得好我们就放心了。打那以后,翠花整整两年和家里失去了联系,姣姣背着他打过几次翠花的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起先村里有人说翠花失踪了,也有人说翠花被人杀害丢进了后海里,后来村里一个从北京当保姆回来的女人私下里说翠花跟人了,男的是一家装潢公司的经理,河南人。 又是一个火热的六月到了,原野里绿绸子似的麦子一片片变成了杏黄色,村子里的庄农户们开始忙乎着下镰前的准备。那天,旺来正蹲在院子里磨镰刃,听见厨房里陪奶奶做饭的姣姣一阵急剧地咳嗽,接着就听老母亲一声尖叫,“姣姣咯血了。”旺来丢下手里的镰刀,赶忙叫来本村一位老中医看了看,老中医背着老母亲和姣姣,对旺来说姣姣的病不轻,医院里去治。第二天街上正好逢集,旺来卖了家里的骡子,从信用社里取出翠花寄来的那五千元钱。从街上回来后,建生来到旺来家,很神秘地给了旺来一个手机号码,说是他媳妇彩梅偷偷告诉他的,到公用电话上去试试。旺来急忙跑到隔壁开铺子的三爷家,在公用电话上拨通了建生给的号码,电话耳机里几声“嘟嘟”的声音后,传来一个苍老的男子声音,你找谁?旺来说了声找翠花。那头一阵低语后,翠花接上了电话。翠花用旺来听不很清楚的普通话说,嗷,是哥呀。旺来一愣,是我旺来。我听出来了,家里都好吧?翠花一问,旺来的声音不由有些哽咽,家里其他都好,就是姣姣生病了,医院里去看,要不就耽搁了。翠花说那就赶紧去看呀。旺来说你到北京几年了,也混熟了,我想把姣姣引到北京去看,你看能行吗?翠花说,医院,就去兰州看吧,来北京花费大。旺来说你不是在大老板家当保姆吗,我们的钱万一不够了你还能让老板借点。翠花说,我是个小保姆,没那么大的面子,你一定要来就来吧。说着“嘟”一声挂了电话。 旺来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和老母亲一商量,老母亲也说去北京好,北京城里啥病都能治,再说翠花几年了没给家里寄钱,手头肯定有积攒,庄里在北京打工的人多,不怕找不到翠花。旺来连夜搭汽车到天水,又坐了一夜火车来到了北京西站。一下火车,旺来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走出站台,一下子茫然了,发现自己和姣姣站在一座悬在半空的铁桥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各色各样的蚂蚁搬家似的小汽车,高得钻进云天的大洋楼一座挨着一座,密密麻麻地看不到头。旺来背着姣姣左顾右盼地顺着天桥走去,刚走到天桥尽头,突然有人在他的肩上拍了一下,转脸一看原来是建生的媳妇彩梅。彩梅手里提着两块考得黄黄的鸡腿,诧异地问你们咋来了,旺来说来给姣姣看病,彩梅说翠花知道吗,旺来说翠花知道姣姣的病,但不知道他们来。彩梅望了一眼伏在旺来背上的姣姣,偷偷叹了口气。旺来问彩梅见没见过翠花,彩梅说没见过。旺来急忙问为啥,彩梅说你们家翠花现在是有身价的人,我们这些当保姆的能随便见吗。一直盯着彩梅看的姣姣突然说,阿姨是你叫我妈来北京的,你肯定知道我妈在哪,你就带我和爸爸去找吧,我已经几年没见我妈了。彩梅摸摸姣姣的头,孩子咱先吃饭去。阿姨,我想妈,好想妈。姣姣说着泪水顺着腮帮滚落下来。彩梅取出一块鸡腿递给姣姣,好孩子咱先吃饭去,吃过饭阿姨带你去找你妈,啊!彩梅说着意味深长地瞟了一脸神情委顿的旺来,走啊! 彩梅带着旺来和姣姣来到车站附近的一家面馆里,给旺来和姣姣点了一大一小两碗牛肉面,旺来面对着冒着热气的面碗只顾发呆,姣姣啜了口面汤,轻轻地一扯旺来的衣袖,爸爸,吃点吧,你有两天没吃一口饭了。旺来木然地点点头,双手捧起面碗,如喝药汤似的抿着嘴吸了一口。彩梅看着眼前这一对可怜的父女,好似自己跌进了苦水缸里,不由得鼻子一酸,两股热乎乎的咸水流进了嘴角。三人默坐了一阵,彩梅对旺来说我自己租了间房,你们先歇在我住的地方,下午我出去打听一下翠花。旺来说,我人生地不熟的,一切听你的,只是太麻烦你了。彩梅说有啥麻烦不麻烦的,都是一个庄里人,走吧。 彩梅住在一个小巷深处的一间平房里,一张已过时的双人席梦思床占去了大半个空间,靠窗墙旮旯里一个玻璃茶几上放着台14吋彩电,茶几旁一个大纸箱里装满了花花绿绿的衣裳。彩梅麻利的整理了一下床铺,扭开立在茶几另一头的落地式电风扇,把一脸倦容的姣姣抱在床上转身出去了。彩梅刚出门,丢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滴滴”地响了起来,旺来愣了愣顺手抓在了手里,不小心触动了接听键,手机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小梅,有个新疆的客人,你接不接?”旺来心里一抖,忙把手机放回了茶几上。不大一会,彩梅手里提着两瓶矿泉水回来了,说家里没开水,让旺来和姣姣先凑合着喝点。旺来瞟一眼彩梅嗫嚅着说,刚才有个男人打你的电话,叫你小梅。彩梅盯着旺来的眼睛问那男的还说啥了,旺来眼看着别处说,说是新疆来了啥客人。彩梅脸一红说,莫管,打错了。彩梅我也想打个电话。彩梅知道旺来的心思,拿起手机说你说电话号码我给你拨。旺来说了那个电话号码,彩梅一怔,谁给你说的这个号码,旺来说是建生告诉他的。彩梅犹豫了一阵拨了出去,一连拨了两次都是空号。彩梅看着焦躁不安的旺来,别指望翠花了,给孩子看病要紧,医院离这里不远,下午我陪你去给姣姣看病。彩梅陪着旺来说了会话,说她出去办点事。等彩梅走后,旺来把电风扇往床跟前挪了挪,望着熟睡中的姣姣心里一声哀叹——我苦命的娃啊! 门外传来一阵轻盈而熟悉的脚步声,旺来!随着一声轻叫,门开处进来一位打扮很洋气的年轻女人,旺来只觉眼前闪过一道亮光,是翠花,真是他的翠花,只见翠花上身穿着奶油色短袖衫,下身是一条橘黄色迷你裙,脚上是一双猩红色高跟凉皮靴,比以前更水灵更好看了,也更富态了。旺来看着翠花心里不由一哽,你咋这么狠心,几年了不给家里一个电话,姣姣生重病了你知道吗?翠花看一眼旁边打着鼾声的姣姣,我知道,这不我来看你和姣姣来了,说着一把搂住旺来的脖子,轻柔而急促地在旺来的脸上亲了起来,旺来酥软的身体里冒出一股股清爽的舒心,嘴里喃喃地叫着翠花,翠花。旺来,旺来,旺来突然觉得翠花的声音变了样,惊诧地睁眼一看,翠花变成了彩梅,旺来痴痴地看着彩梅,搞不清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里。旺来,医院这会上班了,咱走吧。听彩梅这么一说,旺来才完全清醒过来,赶忙叫醒仍在沉睡着的姣姣,跟着彩梅去医院。 医院离彩梅住的地方只有两站路,很快就到了。有彩梅关照着,很顺当的给姣姣挂了号,经过一番透视化验,姓宋的内科主任仔细地看过胸透片和化验单说需要住院治疗,开了个单子让旺来去办理住院手续。旺来嗫嚅着问需要多少钱,医生说先付两万元,以后再看情况。旺来一听两万元,头脑里轰的一声懵在了那里。彩梅看一眼可怜兮兮的旺来,说旺来你来时带了多少钱,旺来带着哭腔说前年翠花寄了五千元钱加上他买骡子的钱总共还不到七千元,我到哪去借一万多元钱啊。旺来说着说着一把抱住姣姣,蹲在地上失声大哭起来,我可怜的孩子,你爸我没用啊!爸爸,我妈有钱,等找着我妈再给我看病吧。姣姣用手给旺来擦着脸上的泪水哭着说。宋大夫扭头看一眼旺来,哭有啥用,赶紧去筹备钱吧。彩梅劝了一会旺来,掏出手机说我再试试翠花的手机通不通,说着拨通了翠花的号码,旺来止住哭声,猛地站起身一把抢过手机紧紧地贴在了自己耳朵上,时间过去了好一会,但他能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隐隐约约的“滋滋”声。彩梅缓缓地从旺来手里抽出手机,抹着眼泪央求大夫帮忙先让姣姣住上院,钱她想办法。大夫疑惑地看着彩梅,你是亲戚?彩梅说我们是一个村子里的老乡,孩子的妈也在北京打工,可好长时间没消息了,恐怕是失踪了。姣姣一听她妈失踪了,泪水涟涟的眼睛里射出一股撕人心肺的绝望而又恐惧的眼神,一把抱住旺来的腿,爸爸,咱去找妈,去找妈啊!姣姣哭着“哇”一口鲜血喷射了出来,旺来裤子上、鞋面上满是滴滴答答的血水。几个闻声进来的护士看到这凄惨的情景一个一个抹起了眼泪。手捏着下巴坐在办公桌前的宋大夫从彩梅手里要过他开的住院单子,和彩梅出去了,不大会儿回来说,让孩子先住下吧。旺来“噗通”跪在地上,头重重地磕着地板,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宋大夫拉起旺来说,不要这样,你们想办法去弄钱吧,我只能担保你们暂时入院。彩梅帮旺来安顿好姣姣,对旺来说,你照看孩子,我去弄钱。 第二天中午,彩梅果然拿来了两沓新崭崭的百元大票子。彩梅说一万是她自己存的,另一万是向别人借的。旺来注意到彩梅说话时眼神有些飘忽,大热天还穿了件高领衬衫,脖颈上围着条印花纱巾,但纱巾掩盖着的领口处,那雪白的脖颈上一块青紫的伤痕还是刺眼地钻进了旺来的眼中。转眼十天过去了,姣姣的病却无多大起色,只是咯血的次数少了,医院通知旺来交的那两万块钱也快用完了,得再预交两万。这天中午临下班前,旺来正在给熟睡中的姣姣擦拭脸上的汗水,姓康的中年护士长手里捏着两瓶娃哈哈饮料轻手轻脚走了进来,放下手中的饮料,看着旺来默默站了会,轻声说,年轻人,这种病是慢性病,治疗周期长,你们农村人经济也不宽裕,再说这种病也没有啥特效治疗方法,我看你还是把孩子领回去找个好中医治吧,中医治疗或许效果更好些。旺来木然的抬起头,死死盯着康护士长的眼睛,你是说我的孩子没救了,我还有几千元钱。康护士长轻叹一口气,同情地说,听我的没错,我是为你好,这两瓶饮料是给孩子的。说罢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旺来出去了。 彩梅已经有三天没来了,旺来失去了唯一的依靠,无计可施的旺来只好办理了出院手续。那天的太阳格外的毒,旺医院大门,只见弥漫着灰黄色雾霭的天宇间不见一丝风,大街上的行人也比平时少了许多,懒懒地爬在停车场里的小汽车一个个反射着刺眼的白光。趴在旺来背上的姣姣伸手抓抓旺来的肩头,喘着气说想吃雪糕。旺来左右一看,见左侧不远处人行道边有个撑着太阳伞卖冷饮的老大娘。医院大门口一个阴影里,穿过斑马线去给姣姣买雪糕。这时,一辆墨绿色医院门口,一个花白头发的矮胖男人从车里出来后,弯下腰伸手从车里搀出一位戴着墨镜,穿着黑裙子的年轻女人。妈妈!坐在阴影里的姣姣一声尖叫跌跌撞撞地朝女人跑去,边跑边扭头叫旺来,爸爸,我妈来了,爸爸,你看我妈来了!矮胖男人搀着的女人条件反射似的身子一抖,扭头看了一眼姣姣,嘴唇一阵哆嗦说小姑娘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妈,说罢扬起头被矮胖医院大门。姣姣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亲亲的妈竟不认得她了,虚弱的小身子一软跌坐在了被太阳的毒光炙烤得冒烟的大理石地板上...... “旅客朋友们,天水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拿好自己的行李。”乘务员轻柔的声音把旺来惊回了现实,神情恍惚的旺来抱着半醒半睡着的姣姣转乘上了来自家乡的返程班车。 旺来和姣姣从北京回来的第28天,也是姣姣十四岁生日那天,早上起来,旺来到街上给姣姣买了个小生日蛋糕,称了一斤姣姣以前最爱吃的夹心饼干,给姣姣第一次过了个正儿八经的生日。吃过早饭,旺来独自拉着架子车到地里去拉麦子。太阳落山时,旺来刚把最后一车麦子拉进打麦场里,远远听见家里传来一片哭喊声,等旺来跌跌撞撞地跑进家门,女儿姣姣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哭成了泪人的旺来母亲告诉旺来,熟睡着的姣姣突然睁开眼说她妈回来了,就站在炕跟前,手抓着炕沿叫了两声妈,就再没醒来。 火热的夏天、沉甸甸的秋天相继悄无声息地溜走了,旺来死灰一样的心迎送着一个个死灰一样的日子。冷酷的冬不可阻挡地来临了,院子里那株曲虬的老榆树昨天还是枝叶婆娑,早上起来已是枝秃叶疏,院子里落了厚厚一层还带着绿意的树叶。旺来正在无精打采地扫着树叶,建生捏着手机急匆匆跑来让旺来接电话,是彩梅打来的。旺来刚把手机接在手里,彩梅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旺来,医院看姣姣,你们已经出院了,等我赶到火车站时你们已经走了。旺来,我给你说件事,你听了不要激动。翠花想见你一面,你来一趟北京吧。旺来嘴唇一阵哆嗦,没等彩梅说完就挂了。旺来刚把手机还给建生,“滴滴”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建生接通听了听再次递给了旺来,彩梅带着哭腔说,旺来,我知道你心里痛,要恨就恨我吧,是我把翠花领到北京的,是我害了你,害了你们一家。旺来淡淡地说,我不怨你,我谁也不怨,我只怨自己命苦。彩梅央求似的说,旺来,你最好来一趟北京吧,翠花叫你有很重要的事。旺来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彩梅,我不会再有啥重要事了,这辈子再也没有了,旺来说着断然挂了电话。 半月后,旺来收到了彩梅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旺来瞄了一眼顺手丢在了屋桌上。旺来母亲劝旺来还是看看吧,不看也是一块心病啊。旺来在母亲的催促下,打开了信封,信封里是翠花的一纸绝笔信。翠花的信是这么写的: 我的夫君旺来(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么称呼你):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我写这封信不是奢望能得到你的宽恕,我只是想把这几年的经历告诉你。那年我到北京后经彩梅介绍在一家饭馆里打工,遇上了开装潢公司的老胡,老胡说他妻子不能生育,让我给他介绍一位年轻健康的农村女人,说是给他生个女儿就给十万块钱,要是生个儿子就外加一套房子,但有个条件,在没生下孩子之前要和家里断了联系。鬼迷心窍的我就自己应承了下来。医院检查胎位,正巧碰上了姣姣,看到姣姣面黄肌瘦的样子,我的心都碎了,我当时多想抱抱姣姣亲亲姣姣,但我不能让老胡发觉啊!旺来,不是我心狠,我是想让咱家也能住上小洋楼过上好日子。现在我虽然得到了一套楼房和足够花半辈子的金钱,但我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失去了这个世界上我最亲的亲人,自打姣姣走后,我整天生活在噩梦里,我的良心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煎熬。我成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廉耻,无情无义的坏女人,我没脸再活在世上了,我要到那边去陪伴我可怜的姣姣,去弥补一个为人母的责任。 旺来,我叫你来北京是想当面给你个交代再结束自己这条罪孽深重的贱命,现在只好写个遗嘱了。我死后这些财产你就看着处理吧,就算是我对你们肖家、对你的一点补偿。翠花绝笔。 旺来看完信,显得很平静,对母亲说了声翠花有消息了,把信和遗嘱揉成一团丢进了母亲煨茶喝的火盆里。 火盆里腾起一股蓝幽幽的火焰。 Watchinterestingmovies作者简介五味子,原名杨瑞峰,甘肃礼县人,生于年6月,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作家协会会员。年以来在国家、省、市级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故事、报告文学等文艺作品近百万字,有多篇小说、民间故事和散文作品被多种选本收录。与他人合著有《礼县民间文学集》,主编出版有《礼县军事志》。现供职甘肃省礼县县委宣传部。 《文化礼县》编辑部 顾问: 赵文博式路王若冰小米 赵殷张中定包苞 (按各位老师受邀时间排序) 小编: 祁新龙夏沫李剑鸣 乔斌琪杨波魏跃军 本期编辑:夏沫 荐稿投稿邮箱:whlxtg sina.治好一位白癜风幸福一个家白癜风权威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shayuanz.com/wwzpz/1363.html
- 上一篇文章: 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年版
- 下一篇文章: 会员分享mela灵芝五味子胶囊帮助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