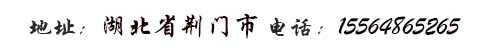2024甲辰年北半球运气用药分析
|
北京治疗白癜风比较好专科 https://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etbdf/人生存于气交之中,与外界的气候环境息息相关。外界的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五运的盛衰、六气的变化以及运气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影响,甚至引发疾病。这些影响和致病途径,主要通过气候与人体脏腑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当气候作用于相应的本脏时,可能会引发本脏的疾病;当气候作用于所胜脏时,可能会引发所胜脏的疾病;当气候作用于脏之后,可能会引起所胜或本气之子的复气来临,从而引发疾病。此外,气候作用于体表、经脉、脏腑的表里关系也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发病及其轻重和证候差异,主要取决于五运六气的属性、运气生化克制关系和人体素质等因素。例如,如果运的土湿太过,就会影响本脏脾(脾胃)的功能,从而引发腹泻等症状;如果土湿过盛,土克水,土湿会损伤肾阳,引发小便不利、水湿泛滥等症状。但是,水之子为木,木能克土,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水之子木会来复,对所胜之土湿进行报复而加以克制,从而又可引发脾的病证(如肝阳上亢之脾不健运等)。以甲辰年为例,这一年的气候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尤为显著。太阳寒水司天,太宫土运太过,太阴湿土在泉。甲为阳干,岁土太过,水受乘,木来复,导致肝风偏胜,脾肾阳虚寒湿。综合甲戌的五运与六气,对于其体质特征可以总结为:易病脏腑为脾肝肾心,病性在上为肝风偏胜,心阳被郁,在下为脾肾寒湿大行。其中岁土太过与之相通应的脾湿过盛为主要体质特点,且客气太阴湿土在泉,湿邪壅盛,加重了脾虚湿盛的特点。在运气相合的分析中,太过的岁土与在泉之太阴湿土五行皆为土,乃同天符之年;岁运之阳土与岁支之辰土相符,乃岁会之年;客气太阳寒水司天,岁运之土克司天之水,运盛而气衰,乃不和之年。因此,综合岁运、司天、在泉的影响下,甲辰年的湿邪淫胜至极,使得脾虚湿盛的体质尤为显著。此外,岁土太过木气来复与之相通应之肝风偏胜温升之力过强。在五运推演中,甲辰年的岁土太过,导致肾水(肾膀胱)受到压制而产生病变,表现为肾阳虚寒的体质。而在六气推演中,客气为太阳寒水司天,寒凝之气偏胜,这也表现出肾水过盛的特点。然而,由于太阴湿土在泉,土克水的效应使得肾水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综合五运和六气的推演结果,上半年肾的功能相对平和,而下半年的肾虚寒凝情况则尤为加重。此外,客气为太阳寒水司天,水乘火,寒湿交争为疟,侵害于火(心小肠),导致心阳被郁,这是另一个特点。 总的来说,甲辰年的体质表现呈现出肝风偏胜、心阳被郁、脾肾寒湿的特点。在发病后,容易出现上风寒中湿下寒的疾病病机特点。其中,脾湿偏胜是病机关键。在太过的岁土、司天之气太阳寒水以及在泉之气太阴湿土的共同影响下,湿邪淫胜至极,使得脾虚湿盛的体质成为本年的主要体质特点,并且使甲辰年成为六甲年中土湿壅盛最重的年份。这种体质主要表现为整体(上中下三焦)偏寒湿,阳气升发不足,阴寒之气弥布。 因此,对于临证治疗中逢甲辰年出生的人群,应注重顾护脾土,温阳健脾祛湿。即使患者没有明显的湿邪症状,也应如此处理。同时,还应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权衡上半年肾水的太过与不及,并注意上半年心火不足的程度。此外,由于土运太过,雨湿流行,若本脏受邪,还可能出现肌萎、足痿、行善瘈(战栗挛痛)、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脾湿过盛不能输布水津而发为饮,不能运化则中满食减)、四肢不举等症状。若肾水受邪(土克水),则可能出现腹痛、清厥(厥冷)、意不乐(肾藏志,志不舒则忧郁不乐)、体重烦冤(肾乃气血之生源,人之行动有赖于气温、血濡,今肾水受邪,气血之源不足,气不足则体重而行动不便,阴血不足不能济阳则阳亢而烦冤)等症状。若至春令,水之子木气盛而来复之,则可能伤脾而使脾反病。若岁土不及,本脏患病则多有留满否塞等症状。若所不胜的风木之气相乘(木克土),则人容易出现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风胜燥化伤津而筋骨失养,故筋骨摇动)、肌肉润酸(肌肉跳动酸痛)、善怒、病寒中等症状。另外,岁土不足时,木来乘而制之(木克土),但土之子金又可乘木之虚而复之(如在长夏,土气不及,则木气来乘,但到秋季金气当令时,则金又来克木),故有胸胁暴痛而下引少腹、善太息(呼气多吸气少而长出气)、食少失味等症状。在辰戌之岁,太阳司天,掌管着整个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太阳作为寒水之气,它的本性是寒冷的,然而表现出来的却是炎热的。因此,当太阳出现异常时,往往会导致一些与本性相反的热症,例如痈疡、呕血、血泄、鼽衄等。此外,太阳的异常还会影响人体的胸腹部位,导致胸腹满闷等症状。太阳的本性寒冷,寒气过盛就会向上侵犯心火,导致心火上炎。当心火受到寒气的逼迫时,就会引发心厥痛、眩仆、面赤目黄等症状。同时,太阳的寒冷还会导致人体内部的水火失衡,出现心烦、善噫、嗌干、渴而欲饮等症状。在心包络方面,心包是心脏的外围结构,可以代心受邪。当太阳病侵袭心脏时,心包络也会受到影响,出现手热肘挛腋肿、心澹澹大动等症状。这些症状都是由于太阳的寒气过盛导致的经脉受阻所引起的。在治疗太阳司天的病症时,需要采用辛热之药来散寒,同时还需要用甘苦之药来制水。其中,甘为土味,可以补益脾土;苦为火味,可以补益心火。同时,还需要用咸味药物来泻下寒水之气。与此同时,太阳司天则太阴在泉,太阴代表着湿土之气。当太阴出现异常时,会导致三焦、肾、膀胱等水脏受到损害。具体来说,太阴湿土之气过盛会导致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等症状。此外,还会出现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等症状。这些症状都是由于太阴湿土之气过盛导致的经脉受阻所引起的。在治疗太阴在泉的病症时,需要采用苦热之药来燥湿,同时还需要用酸淡之药来制土和渗湿。其中,酸为木味,可以制土;淡能利窍,可以促进湿气的排出。通过这些治疗手段,可以有效地调节人体的气机,恢复健康。 1.司天之气淫胜治则 在中医理论中,太阳寒水司天的年份,寒邪淫盛成为主要病因。此时的治疗原则为:“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然而,此处的治疗原则顺序似乎存在问题,应当与“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保持一致,即正确的顺序应为“寒淫所胜,平以甘热,佐以苦辛”。寒邪为水气所化,土能克水,甘味从土化,而热能克制寒邪。因此,应以甘热之药为主,以平息寒邪。此外,苦味之药能顺其气而坚实之,对于补肾水有良好效果。中医认为,“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这正是苦味药补肾水的道理。同时,水寒之气郁结不散时,会导致津液失布。辛味之药能开腠理、致津液、通诸经之气而散水气,濡润四肢百骸。中医认为,“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这正是辛味药润燥的原理。因此,以苦辛之药为佐,既能防止甘热太过而伤及本气,又能助甘热辛散寒气。最后,咸味之药与水气相通,能够反其性而软化凝结的水气。因此,咸味之药具有泻肾水的作用。故以咸泻尽去寒邪之源。 2.在泉之气淫胜治则 在中医理论中,太阴湿土在泉,湿邪淫胜的治疗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的论述,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这意味着在湿邪过胜的情况下,治疗应以苦热为主,酸淡为辅,苦味药能燥湿,淡渗利窍可以去除湿邪。首先,苦味药是治疗湿邪淫胜的主要药物。这是因为苦味药具有燥湿的作用,能够祛除体内的湿气,使湿邪得以清除。同时,苦味药还有泻下的功效,能够通腑降浊,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清除体内的湿邪。其次,酸味药和淡味药也是治疗湿邪淫胜的重要辅助药物。酸味药可以收敛固涩,止汗止泻,有助于调节身体的各项生理功能。而淡味药则具有利尿的作用,能够促进体内水分的排出,从而有助于清除体内的湿邪。此外,《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提到:“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这意味着苦味药虽然能够燥湿,但如果过量使用则会损伤脾胃,影响消化功能。因此,在使用苦味药时需要注意适量,避免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综上所述,对于湿邪淫胜的治疗,应以苦热为主,酸淡为辅。同时需要注意药物的用量和使用方法,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3.太阳寒水之气胜治则 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泻之。此言火胜之治也。火胜则水败,故治当补火泻水。然而,火为阳邪,易耗气伤津,故需以甘温之药扶正益气,热则火得温而愈烈,可益心火,使心阳得振,血脉流畅。甘为土之正味,可平水邪,使水邪得制。火土相生则水有制而火不受克,故治以甘热。若药力不足,则水寒之气郁结不散,津液失布。此时,需佐以辛味之药。辛性散,能开腠理,致津液,通诸经之气而散水气。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言:“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此之谓也。辛温药能润燥、散寒、化气,使水寒之气得以宣散。然而,甘温药力太过,又有伤津耗气之虞。故需佐以酸味之药,以顾护气津。酸味收敛固涩,能生津液,使津液不致耗散太过。同时,酸味还能制约甘温药的温燥之性,使其药效平和。水性凝滞收引,故需用咸味之药反其性而软之。咸能软坚散结,渗利水湿,使水邪从小便排出体外。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以咸泻之”,此之谓也。附子山茱萸汤便是依此法而设。方中用大辛大热的附片、辛温的丁香以温肾壮阳而除寒湿;用酸温的山茱萸以滋补肝肾;用酸平的乌梅、辛温的肉豆蔻以涩肠止泻;用辛温的藿香、半夏以化湿燥湿;用酸温的木瓜和胃化湿、舒经活络。合而有温阳祛寒、和胃化湿止泻之功。肾着汤原名甘草干姜苓术汤,为《金匮要略》中治肾着之方。其病之发生是由于身劳汗出、衣裹冷湿而久久得之,症见有“身重腰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这些病症均属于肾受寒湿之邪,着而不去,以致形成肾着之病。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治疗土运太过致肾经受湿之证的方法来治疗此病。所列病症虽与原方主治之症不尽相符,但二者之病因均属寒湿之邪为害,取其“异病同治”之法。方中又加猪苓、泽泻者,以增强利水湿之功,并有分清浊以止溏泻之效。 初之气(1月20日-3月20日):主气厥阴风木,客气少阳相火。 若主气厥阴风木胜,其治则为“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素问?至真要大论》)。木性升,酸则反其性而敛之,故为泻。辛则助其发生之气,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此之谓也。 若客气少阳相火胜,其治则为“少阳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咸软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火欲软,咸则顺其气而软之,故为补;火性烈,甘则反其性而缓之,故为泻。《素问?脏气法时论》言“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写之”,此之谓也。咸补火本于其软,故“软”即为“补”,故曰“以咸软之”。 少阳相火加临厥阴风木,风火同气,故其所发病症为病温,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皆属风热之症,所以用防风通圣散以解表通里、疏风清热。该方曾主治憎寒壮热、头目昏眩、目赤睛痛、口苦口干、咽喉不利、胸膈痞闷、咳呕喘满、大便秘结、小便赤涩,以及疮疡肿毒、肠风痔漏、惊狂谵语、斑疹等,故此处选用本方来治疗风热肿毒之证。方中用防风、荆芥、薄荷、麻黄疏风解表,大黄、芒硝泻热于后阴,栀子、滑石泻热于前阴,桔梗、石膏、黄芩、连翘以清肺胃之热,当归、川芎、芍药和血以祛风,白术、甘草健脾益气,从而达到表解里清,则身热、头痛、肌腠疮疡等症自消。方中药物性味的配伍法则尚符合《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的风火淫胜病症治则。 二之气(3月21日-5月20日):主气少阴君火,客气阳明燥金。 若主气少阴君火胜,其治则为“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素问?至真要大论》)。火性烈,甘则反其性而缓之,故为泻。火欲软,咸则顺其气而软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此之谓也。 若客气阳明燥金胜,其治则为“阳明之客,以酸补之,以辛泻之,以苦泄之”(《素问?至真要大论》)。金性敛,辛则反其性而散之,故为泻。金欲收,酸则顺其气而收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此之谓也。苦从火化,能泻燥邪之实,若燥邪未尽,则复以苦泄之。《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此之谓也。 阳明燥金加临少阴君火,火热为清凉之气所遏,则病发为气郁中满,故可用栀子豉汤主治。栀子豉汤出自《伤寒论》,原主治热扰胸中的心中懊侬症。二者表现虽不尽相同,但其病机皆属热郁所致,故可用同一方来治疗。 三之气(5月21日-7月22日):主气少阳相火,客气太阳寒水。 若主气少阳相火胜,其治则为“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素问?至真要大论》)。火性烈,甘则反其性而缓之,故为泻。火欲软,咸则顺其气而软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此之谓也。 若客气太阳寒水胜,其治则为“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水性凝,咸则反其性而软之,故为泻。水欲坚,苦则顺其气而坚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此之谓也。因苦补水本于其坚,故“坚”即为“补”,故曰“以苦坚之”。因水寒之气郁结不散,津液失布。辛性散,能开腠理,致津液,通诸经之气而散水气,濡润四肢百骸,《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此之谓也,故以辛润之。 太阳寒水加临少阳相火,也是火为寒水之气所遏,故有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等,属上热下寒、寒热错杂之证。因此,可用寒热并用的乌梅汤(丸)来主治,其药物性味的配伍法则也基本符合《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的寒火淫胜病症之治则。方中各药之分量已如前述。 四之气(7月23日-9月22日):主气太阴湿土,客气厥阴风木。若主气太阴湿土胜,其治则为“土位之主,其泻以苦,其补以甘”(《素问?至真要大论》)。土性湿,苦则反其性而燥之,故为泻。土欲缓,甘则顺其气而缓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此之谓也。 若客气厥阴风木胜,其治则为“厥阴之客,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发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木性升,酸则反其性而敛之,故为泻。辛则助其发生之气,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此之谓也。风木偏胜,易出现肝阳上亢、肝火上炎、肝风内动等证,临床出现拘急、痉挛、掉眩等“肝急”表现,甘能缓急,故以甘发之,《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也”,此之谓也。 厥阴风木加太阴湿土,木可克土,故病发大热少气、注下赤白等风热和湿热之症。所以,可借用治疗热痢、下重的白头翁汤主治,以清热平肝止痢,况且该方在《伤寒论》中本属厥阴病方,方中的白头翁清热凉血、黄连与黄柏清热燥湿、秦皮清热燥湿凉肝以止痢。若偏湿,以致太阴脾为湿困,不能转输水谷之精气而发为肌足萎者,则改用理中汤(丸)主治,取其理中汤(丸)为太阴病主方之意。 五之气(9月23日-11月22日):主气阳明燥金,客气少阴君火。若主气阳明燥金胜,其治则为“金位之主,其泻以辛,其补以酸”(《素问?至真要大论》)。金性敛,辛则反其性而散之,故为泻。金欲收,酸则顺其气而收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此之谓也。 若客气少阴君火胜,其治则为“少阴之客,以咸补之,以甘泻之,以酸收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火性烈,甘则反其性而缓之,故为泻。火欲软,咸则顺其气而软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泻之”,此之谓也。热盛于经而不敛,反伤阴耗气,故以酸收上炎之火气,顾护微弱之气阴。《素问?脏气法时论》言“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此之谓也。 临床上根据四诊合参辩证的基础上加麦冬,北沙参、姜半夏,淡竹叶。 终之气(11月23日-年1月19日):主气太阳寒水,客气太阴湿土。若主气太阳寒水胜,其治则为“水位之主,其泻以咸,其补以苦”(《素问?至真要大论》)。水性凝,咸则反其性而软之,故为泻。水欲坚,苦则顺其气而坚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此之谓也。 若客气太阴湿土胜,其治则为“太阴之客,以甘补之,以苦泻之,以甘缓之”(《素问?至真要大论》)。土性湿,苦则反其性而燥之,故为泻。土欲缓,甘则顺其气而缓之,故为补。《素问?脏气法时论》言“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此之谓也。甘补土本于其缓,故“缓”即为“补”,故曰“以甘缓之”。应温中散寒,益气健脾、清热,应加制附片、干姜、荜澄茄、茯苓、炙甘草、木瓜等。 #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eizia.com/wwzpz/13309.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味奇妙的中药,不仅抗衰老抗肿瘤调免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